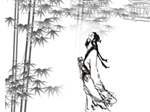前言:
董其昌力行仿古,但是又不肖形似,其山水作品也遠離自然主義的色彩。在理論層面上董其昌自有他解決的辦法,自然和古人的傳統只有在畫家的心中才能夠同時存在,且其二元對立的現象才會彼此消解。畫家要在自然山水世界中有所感悟,并將最終歸于自己的內心世界中,把源于內心的情感領悟轉化于筆法,墨跡,通過描繪的方式表達出來,是藝術家心印的投射。董其昌不必向古人低頭,不屈服于自然與古人之間任意取舍。董其昌利用自己的地位增強自己的話語權,繪畫本身就是社會精英,上層人士在閑暇之余的精神享受,他利用自身具備的充分的藝術史知識,以及在創作及鑒賞時,具有的高度品位,來滿足士紳文人圈子的愛好,以符合他們的審美模式及視覺觀看體驗。

中國繪畫史
作者:水木清楊
29.9幣
4人已購
筆墨傳達性靈,直指本心,直入如來地
董其昌含蓄地批評吳門畫家重理,強調松江畫家重筆,陳繼儒則講得更清楚:“文人之畫不在蹊徑,而在筆墨。“倪元璐則提出”“以性靈傳筆墨”。筆墨傳達性靈,直指本心,直入如來地,是董其昌”南宗“畫論的主旨。
在董其昌的筆下,狀物已非目的,只要性之所致,山石可以任意扭曲,樹木無須分遠近。如他石間常留白,既非受光面,又非與山石結構有關,似乎是視覺或心理趨筆成形,又如他畫近景大樹腳下,常如點苔般畫上一些小樹,比例懸殊,尺寸有時比遠景樹還小。這種比例失調。遠近錯位的畫法并非有意而為,也不影響畫面整體效果,因為歸根結底,他的畫面內容是筆墨而非山水,董其昌駕馭筆墨達到相當自由的境界,并把狀物手段的筆墨提升到繪畫內容本身,這在繪畫史上是合乎邏輯的演變。
氣韻藏于筆墨,筆墨都成氣韻
龔賢提出的“畫家四要”。筆法,墨氣,丘壑,氣韻,把筆墨與內容(丘壑),效果(氣韻)列為對等的要素,稱“必筆法,墨氣,丘壑全,而后始可畫”。
王原祁認為氣韻生動乃在于用筆用墨,他說:“用筆用墨,相為表里,氣韻氣動是也”。惲壽平講得更明白:“氣韻藏于筆墨,筆墨都成氣韻”,氣韻的概念,最初指人物的精神狀態,雖然六朝以后,其內涵不斷擴大,但是總是與自然生命的律動有關。
確立了筆墨作為繪畫中心內容的新原理
董其昌之后,畫家普遍強調筆墨的重要性,并與傳統畫論的第一要義“氣韻生動”聯系起來,提到對等的地位,從而在理論上確立了筆墨作為繪畫中心內容的新原理。這一原理的確立,標志著中國繪畫史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雖然,一些畫論重復狀物寫形的原理,但在內涵上強調的是心性而非外形,李日華闡述的是繪畫創作中達到物我雙忘的境界,實際上強調的乃是筆墨傳達性情。
石濤在近代被描寫成“正宗畫派”的對立面,代表“革新精神”的人物,但實際上石濤的“無法”為“至法”的思想,與董其昌“一超直入如來地”的“南宗”畫論,都受禪宗影響,應是殊途同歸。二十世紀,許多藝術家希望找一個塞尚式人物,石濤就剛好符合這個條件,劉海粟,吳冠中都不約而同推薦石濤為中國現代藝術之父。
石濤《苦瓜和尚畫語錄》中強調,“一畫”說的核心乃是筆墨傳達性情,石濤對泥古不化,他仍是承元四家傳統,早年的畫法度謹嚴,中年后清剛奔放,也是玩弄筆墨的高手,實際上石濤無論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沒有超越當代的時代潮流。
寫意往往被誤解成“逸筆草草”。
董其昌之前的陳淳,徐渭筆墨恣肆,遺貌取神,最為后世所推崇。十八世紀的揚州畫家不少人深受其影響。陳淳,徐渭以行草筆意入畫,舍狀物寫形而達到自由的表現,被視為寫意畫的代表畫家。然而,寫意往往被誤解成“逸筆草草”。
中國畫的本質是“寫意主義”
寫意是“創作方法”而不是繪畫風格,在近代,把“寫意”與“工筆”相對,已經是不合邏輯。寫意是相對寫生而言,工筆是相對率筆而言,寫意可率筆,亦可工筆,寫生可工筆,亦可率筆。但無論工筆,率筆,也無論水墨,重彩,中國畫的本質是“寫意主義”,從西方寫實主義傳統出發,批評中國畫的寫實主義,是很不妥當的。
董其昌無論在書法或繪畫上,都是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大師。
錢詠認為“只要有筆有墨,便是名家”。不難看出,董其昌之后,筆墨已成為中國繪畫的中心議題,大有“藝術語言決定一切”的味道。而有筆墨,有自己的自家面目,皆可卓然成家,名傳后世,董其昌無論在書法或繪畫上,都是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大師。
結語:
董其昌的成功并非偶然巧合,他勇于探索嘗試,不斷求新求變,富于創造和試驗精神,對既定目標有堅定的信念和不懈的追求,董其昌最為過人之處是他能夠認清自身優勢,善于利用自己的價值,并且善于抓住把握時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