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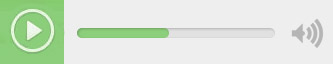 我們都是活的生命體,你知道這有多么不容易嗎?就人類目前所知,在整個宇宙中,只有這么唯一的一個地方,也就是在銀河系一個毫不起眼的角落中的藍色星球愿意收留你,這個星球我們叫她——地球。或許,連地球也可能是不太情愿的。 因為,從最深的海溝底部一直到最高的山巔,所有已知的生命所生存的空間僅僅只有 20 公里厚,與整個地球相比,實在微不足道。與浩瀚的宇宙相比,更是可以忽略不計。  而作為人類的我們,生存空間就更小了。4 億年前,有一些生物做出了一個草率而冒險的決定,它們從海洋中爬到了陸地上,開始呼吸氧氣。這樣一來,這世界上至少有 99.5% 的宜居空間從此基本上、也可以說是完全與它們絕緣了。而我們人類正是這些生物中的一員。 我們不僅無法在水中呼吸,而且更是無法耐受水的壓力。水的比重是空氣的 1300 倍,因此在水中壓力增加得非常快,每下潛 10 米就相當于增加一個大氣壓。在陸地上,如果你在 150 米高的寫字樓中工作,氣壓的變化是很小的,你不會有什么感覺。但是,如果你潛入水中同樣的深度,你的血管就會被壓癟,肺會被壓縮成僅僅只有一個橘子的大小。但讓人驚訝的是,居然有人喜歡不穿戴任何潛水裝備,下潛到那個深度,僅僅只是為了好玩,這種驚險的運動被叫做“裸潛”。看來,有人覺得體內的器官被壓得變形是一種很刺激的體驗,不過,經歷器官恢復原狀的體驗恐怕就不那么刺激了。想要下潛到那種深度必須是在重物的拖曳下,以極快的速度下沉才能達到。在這個領域,有一位大神,他就是奧地利人赫伯特·內奇,這是一位真正的大神,他在國際自由潛水協會認可的八項自由潛項目中都保持著世界紀錄。他去過的最深地方是水下 253.2 米,時間是 2012 年 6 月 6 日,地點是在希臘的圣托里尼島,這是迄今為止,不借助潛水艇,人類潛入過的最深處。他在最深處沒有停留,迅速返回,在返回的途中他還失去了意識,但最終還是成功地活著回到了水面,身體遭受了一些不可逆的神經損傷。但是,這個深度記錄,隨隨便便一條魚就能打破。即便是像抹香鯨這樣生活在水中,時不時還要浮出海面換口氣的哺乳動物,可以輕松地下潛到 2000 米的水下,舒舒服服地呆上 2 個小時再游上來換口氣。所以說,即便我們興奮地完成了這種驚險特技,但恐怕我們也沒資格宣稱自己是深海的主人。 但是另外一些生物卻能成功地挑戰任何深度,只是到底有多少種這樣的生物依然還是個謎。地球上最深的洋底是太平洋中的馬里亞納海溝,最深處達到了 11034 米,壓力達到每平方英寸 7 噸多。2012 年 3 月,曾經執導《泰坦尼克號》、《阿凡達》等眾多大片的著名導演卡梅隆,獨自乘坐潛艇“深海挑戰者”號,下潛到了馬里亞納海溝的最深處,直達溝底,引起了全世界的轟動,這是人類第二次來到這個地球的最深處。上一次還是 1960 年,瑞士人皮卡德乘坐“的里雅斯特”號首次達到溝底。人們發現,在那個深度,居然是端足目生物的領地,這是一種甲殼綱生物,長得像蝦米,只是全身透明,它們就這么在毫無保護的狀態下好好地活著。當然,大多數海洋都要淺得多,但即便是在平均 4000 米的洋底,也相當于壓在 14 輛滿載的水泥卡車下面。 有很多人認為,在深海的巨大壓力下,我們的身體會被徹底壓扁,包括一些海洋學的科普作家也是。其實這個認識不對,我們身體本身的主要成分就是水,而水“實際上壓不扁”,這是牛津大學的阿什克羅夫特說的,“人體內部的壓強會與周圍的水壓保持一致,因此在什么深度也不會被壓碎。”實際上真正帶來麻煩的是人體內的氣體,尤其是肺中的。這些氣體確實會被壓縮,但我們并不知道壓縮到什么程度就會致命。直到 2008 年前后,人們還以為只要下潛到 100 米深度,肺就會內爆,胸腔壁就會破裂,人也會痛苦地死去。但那些裸潛者卻反復證明這是錯的。用阿什克羅夫特的話來說,人類似乎“比預想的更像鯨或者海豚。” 不過,潛水的危險也來自別的地方,有些看似不起眼的設計會出大問題。過去有一段時期,潛水服上有一根長長的管子通到水面,通過水面上的氣泵來給潛水服加壓。但是,身著這樣裝備的潛水員有時會遇到一種極恐怖的現象,當水面氣泵失靈導致潛水服災難性地失壓時。空氣會迅速地離開潛水服,產生一股巨大的吸力,把潛水員整個地吸入潛水面具和管子中。當潛水員被拖出水面后,“潛水服中只剩下一點兒骨頭渣和粘著血肉的破布”。這是生物學家霍爾丹在 1947 年寫下的文字,他生怕人們不信,還特地加了一句,“這事真的發生過。” 順便說一下,最早的潛水面具是一個叫查爾斯·迪恩(Charles Deane)的英國人設計的,只是最初的設計并不是用來潛水,而是用來救火。因此它被叫做“煙火面具”,由于是用金屬做的,所以又熱又累贅,而且迪恩很快發現,消防員實際上都不穿任何裝備就迫不及待地沖進火場中,更不要說戴上燙得像開水壺、還會讓他們變得笨拙的面具了。為了挽救他的投資,迪恩在水下試了試,發現這種面具用于海上救助工作倒是很理想。  在深潛時真正可怕的敵人是減壓病(這個病的英文單詞是bends,意思是“彎腰”)。之所以說它可怕,并不特指它所引起的人體不適,當然不適是肯定的,而是指它很容易發生。我們呼吸的空氣 80% 是氮氣,如果人處于高壓的環境中,那么身體中的氮氣就會溶解在血液中,在血液和細胞組織中游走。一旦氣壓發生劇烈變化,比如在潛水員快速上浮時,那些滯留在人體內的氮氣就會泛起泡沫,就像你剛打開一瓶香檳時看到的那樣,導致的后果就是血管堵塞、細胞缺氧,同時會引起劇烈的疼痛,疼得人直不起腰來。這就是這個病名 bends 的由來。 在過去,減壓病是一種職業病,常見于采海綿和珍珠的潛水員中。但在 19 世紀之前,這種病并沒有引起西方世界的重視。其實這種病還見于另外一群不入水的特殊人群中(準確地說,水不會浸過他們的膝蓋),他們是沉箱中的工人。沉箱是在建橋的時候沉入河床中的密閉干室,里面充滿了壓縮空氣。當工人們在這樣一個人造的高壓環境中長時間工作后再出來時,常常會出現皮膚刺痛和瘙癢的輕微癥狀。但是,無法預料到的是,少數人會持續關節痛,偶爾還會有人痛得倒地,有時就就會再也起不來了。 這些都令人費解。有時候工人們在睡覺前還好好的,但一覺醒來卻癱瘓了,甚至再也醒不過來了。阿什克羅夫特講過一個發生在修建泰晤士河新隧道時的故事。當工程收尾的時候,包工頭搞了個慶祝活動。當他們打開香檳時,卻驚訝地發現沒有泡沫。這是因為隧道中充滿的都是壓縮氣體。當他們在倫敦的夜色中再次呼吸新鮮空氣時,香檳立即泛起了泡沫,這難忘的經歷激起了他們的好胃口。 對付減壓病,除了盡量避開高壓的環境之外,還有兩個方法可以有效地避免減壓病。第一個方法是把經歷氣壓變化的時間減少到很短的一小會兒。另一個方法是非常小心緩慢地上浮,這樣可以使氮氣小氣泡安全地散逸掉。喜歡裸潛的人還發明了一種小技巧,他們在下潛前一般都會拿個空瓶子,在下潛最初階段把肺部的一小部分氣體儲存到瓶子內,等下潛到 100 米以下再吸回嘴里用來平衡耳壓。 我們能夠知道這些知識,要歸功于一對杰出的父子。他們是斯科特·霍爾丹和 J. B. S.霍爾丹(John Scott Holdane & J. B. S. Holdane)。即便是在怪人輩出的英國知識分子圈中,霍爾丹父子也絕對堪稱為怪人。老霍爾丹 1860 年出生于一個蘇格蘭貴族家庭(他哥哥是霍爾丹子爵)。不過他的一生大部分時間都過得很低調,只是牛津大學的一名生物學教授,是出了名的會走神。有一次,他妻子讓他上樓去換一套參加宴會的衣服,結果他一去不回。找到他時卻發現他穿著睡衣躺在床上。老霍爾丹被搖醒后,他說發現自己在脫衣服,以為該睡覺了。他認為的度假就是到康沃爾去研究礦工們的鉤蟲病。小說家托馬斯·亨利·赫胥黎曾經和霍爾丹父子一起住過一段時間。于是,這對父子很不幸地成為了他小說中那位怪癖科學家的原型。我這里插一句,歷史上出名的叫赫胥黎的人很多,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被稱為達爾文的斗犬的生物學家阿爾多斯·赫胥黎,他的孫子就是小說家托馬斯·亨利·赫胥黎,也很出名。 霍爾丹計算出了從深海上浮時,為了避免得減壓病,所必須的休息間距,這是他對潛水事業做出的重要貢獻。不過他的興趣很廣,涵蓋了生理學的主要領域,從登山者的高原病到沙漠地區的中暑問題,都是他研究的對象。其中最主要的一個興趣點是研究毒氣對人體的影響。為了搞清泄漏的一氧化碳到底是怎么奪去礦工的生命,他很有計劃地逐步毒害自己,仔細地抽取自己的血樣做分析。直到他幾乎要喪失對全身肌肉的控制,血液中一氧化碳的飽和度達到了 56%,按照諾頓(Trevor Norton)在他的一本描寫趣味潛水史的書,《海底之星》(Stars Beneath the Sea)中所寫的,再多那么一毫就可以送了他的命。 霍爾丹的兒子杰克(后人一般把他叫做J. B. S.)是一個神童,據說在嬰兒期就已經對他老爸的工作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在他三歲的時候,有人聽到他生氣地問爸爸:“到底是氧化血紅蛋白還是羧基血紅蛋白啊?”在他的整個青少年時期,小霍爾丹一直就是他父親的實驗助手。10 來歲的時候,父子倆就常常一起吸入各種氣體,測試防毒面具,還輪流觀察對方什么時候昏過去。 盡管 J. B. S. 霍爾丹從未取得過科學方面的學位(他在牛津學習的是古典文化,也即古希臘和古羅馬文化),但他靠著自學成為了一位杰出的科學家,大部分時間待在劍橋為政府工作。一生從事智力奧林匹克競賽相關工作的生物學家梅達沃(Peter Medawar)對他的評價是“我所認識的最聰明的人”。作家赫胥黎也沒有放過年輕的小霍爾丹。在他的小說《古怪的圓舞曲》中的(Antic Hay)的主角就是以他為原型的。赫胥黎的那本《美麗新世界》(BraveNew World)就是受到他關于人類基因操縱想法的啟發而創作的。在其他成就方面,小霍爾丹還在一種被遺傳學家稱為“現代綜合進化論”(有時候也叫現代達爾文主義)的理論中起到了關鍵作用。該理論是將達爾文的進化論原理和孟德爾的在基因方面的工作相結合的產物。 還有件事讓小霍爾丹成為人類中的異類,他竟然認為參加一戰是“一次愉快的經歷”,還直言不諱地承認“享受殺人的機會”,他自己在戰爭中也二度受傷。戰后,他成了一位成功的科普作家,一生寫了 23 本書(以及 400 多篇科學論文)。他的書到現在依然具有可讀性,很吸引人,只是太不容易找到了。他還是一名熱忱的馬克思主義者,有人說這是出于他唱反調的本性使然。如果他出生在蘇聯,他很可能就會成為一名狂熱的保皇派了,反正就是要和別人反著來。不知道為啥,腦子里面全是平哥的畫面。不管怎么說,他的許多文章都是首次發表在共產黨創辦的《工人日報》上。 老霍爾丹的興趣集中在礦工安全以及各種中毒癥狀上,而小霍爾丹著迷的卻是如何讓潛艇乘員和潛水者擺脫因工作而引起的痛苦。在海軍部的資助下,小霍爾丹建了一個減壓艙,他把它稱為“高壓鍋”。那是一個可以密閉的金屬圓筒,一次最多可以容納三個人,用于各種危險和痛苦的實驗。志愿者被要求坐在冰水上面,呼吸著“非正常空氣”,或者經歷快速的氣壓變化。在某一次實驗中,小霍爾丹自己在里面模擬危險的海底上浮,他想看看會發生什么,結果發生的是他補牙的材料暴裂開來。諾頓在書中寫道,“幾乎每一次實驗,總是以某人的痙攣、出血、嘔吐而告終。”減壓艙是隔音的,所以里面的人想要表示不舒服或是痛苦,除了不停地敲擊艙壁或是在小窗上貼紙條,別無他法。好吧,講到這里,我腦子里面全是電影《黑太陽 731》的畫面。 在另一次實驗中,霍爾丹由于高濃度的氧中毒而產生劇烈的,摔折了幾節椎骨。對他來說,肺部擠壓是常有的危險,耳膜穿孔更是家常便飯。但是他卻在一篇文章中安慰別人說,“耳膜一般自己會愈合。如果耳膜穿孔一直在,雖然會有一些耳背不假,但是你吸煙的時候,可以從耳朵中吹出煙來,你就會成為大伙談論的焦點,這不也算得上一項社交成就嘛。” 小霍爾丹為了追求科學,愿意冒風險,忍受痛苦。但這不是他最厲害的地方。他最厲害的是能夠不費太大力氣說服同事或者別的什么人爬進減壓艙。在一次模擬下沉實驗中,他老婆發生了痙攣,并持續了 13 分鐘。最后好不容易停止了在艙內的翻滾,霍爾丹把她扶了起來,打發她回家做飯。小霍爾丹還很樂意讓在場的人參與試驗,甚至還包括西班牙前首相內格林(Juan Negrin)。那次實驗相當令人難忘。內格林博士事后抱怨說有一點兒刺痛,并且“嘴唇上有一種奇怪的滑溜溜的感覺”。好在他似乎沒受到什么傷害,估計事后回想起來也是會后怕的。在一次模擬缺氧實驗后,小霍爾丹的臀部和脊柱下段失去知覺長達 6 年之久。 在小霍爾丹眾多癡迷的研究項目中,氮氣中毒現象是其中之一。在水下 30 米深處,氮氣就會開始溶于血液,這時候就會發生像醉酒一樣的氮氣中毒現象,對其中的原理我們目前了解的還不多。當潛水員發生氮中毒現象時,他們會出現幻覺,有的人會試圖把空氣管子遞給魚兒們使用,有的人則會想要抽支煙休息一會兒,有的人情緒會產生劇烈波動。在一次實驗中,小霍爾丹注意到,被試者“在沮喪和高興之間來回切換,前一分鐘還感到難受極了,要求減壓,下一分鐘又哈哈大笑,想要去干擾同事的靈敏度測試。”為了測量這種情況的變化速度,研究人員不得不和志愿者一起鉆進減壓艙,進行一些簡單的定量測試。但是小霍爾丹后來回憶說:“過不了幾分鐘,測試者和被測者都一起中毒,要么會忘了按下秒表的暫停鈕,要么就是忘了做記錄。”即便到了現在,氮氣中毒的原因仍然不很清楚。有人認為這和酒精中毒的原理是一樣的,但缺乏可靠的研究。 好了,講到這里,各位可能會覺得有點抓不住我本期的主題到底想說什么。其實,這只是我很龐大一個話題的開端,我今天從潛水講到減壓病再講到氮氣中毒,其實,我是想告訴大家,如果沒有特別的保護措施,人一旦離開了我們世世代代習慣生活的地球表面,不管是往下面走,還是往上面走,都會陷入大麻煩中。我要給大家講述一個有關我們生命自身的大故事,今天只是一個小小的序章,壯麗的生命詩篇僅僅開了個頭。下一期,我會讓你感受到我們來到這個世界上,能夠活動和思考是一件多么幸運的事情。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