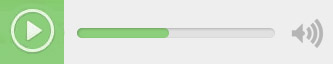在《熬過孤獨的人才配說未來可期》這本書中,作者以“孤獨”為切入點,解析了現代社會里人們為什么會產生孤獨感,以及如何學會在孤獨中更好地自處,建立強大的內心,找到自己的方向。
如果我們能學會孤獨行走,無視別人異樣的眼光,不放棄對生活的熱愛和執著,就能獲得真正的心靈成長。

穿越孤獨的迷茫,才能獲得新生
書中,印象深刻的是寫手阿萌的故事。
阿萌是一個不喜歡張揚的人,在一所不知名大學讀書的他,喜歡一個人安靜地思考寫作,一個人吃飯,一個人走路,一個人泡圖書館。
因為他的特立獨行,身邊的很多同學都笑話他,排擠他。
可他卻依然故我。阿萌并不是沒有朋友,只是他的身邊沒有合適的交談對象,在三觀相合的朋友面前,他立馬蛻變成“話嘮”。
當他后來小有成就后,他的不合群也有了正向的反饋。其實朋友并不是刻意找來的,而是相互吸引來的。
在看到這一段時,我內心特別有共鳴。
因為在單位,我也習慣一個人獨來獨往,我行我素。
以前在單位食堂吃飯時,最怕別人問:怎么一個人吃飯啊?每當這時,我的心里就會泛起一種異樣的情緒,好像我自己就是一個異類。
曾經我想改變這個“孤僻”的標簽,吃飯時刻意和同事們坐在一起,想讓自己變得合群點,可有時候磁場不對,看起來就是那樣的尷尬和不搭。
后來,我沒有再刻意融入同事的圈子,而是選擇接納自己,享受這種孤獨,和一些要好的同事一起吃飯,怡然自得,反而擁有了一些可以相互談心,交流的朋友。
和而不同,親密有間,適度的距離感,這也是人際交往的法則,舒適適度就好。
下班后的時光里,我會閱讀一本好書,寫寫文章。
清晨,我也會和老公一起去公園晨練,看看流動的小溪,青山綠水,脫離了塵世的喧囂,感受生活的美好。
正如作者所說:在如今這個高度現代化的社會,每個人的自我意識覺醒了,我們沒必要為了所謂的合群,去浪費自己的寶貴時間,讓自己不快樂。
穿越孤獨的迷茫,不斷認識自我,接納自我,我們才能獲得新生。
當我們不再害怕孤獨,學會獨處,能忍受那些寂寞時光,不再努力融入身邊人的圈子力求認同,擁有更多的自我認同感,內心也會越來越強大。

孤獨期,也是人生的蟄伏期
孤獨期,也是人生的蟄伏期。這是這本書帶給我的第二個感受。
就像19世紀美國女詩人艾米莉·狄金森,從25歲開始棄絕社交,過著一種隱居般生活,沉浸在自己孤獨的小天地里。
在這種與世隔絕的孤獨中,她留下詩稿1700余首,她的詩歌生前只發表了7首,其余的都在她死后才面世,被世人所知,震驚整個美國文壇。
我并不是鼓勵大家都像艾米莉·狄金森這樣與世隔絕,而是我們在孤獨無助的時候,不妨沉浸在這種孤獨中,或許能打開自己生命的另一扇窗口。
文學家汪曾祺,就是這樣。
下放勞改的時候,汪老負責照看一片果林,閑暇無事的時候,他就靠畫馬鈴薯度日,每畫完一個馬鈴薯后,他會把馬鈴薯放在灶上烤著吃。
為了度過那段難熬的時光,汪老把不同種類的馬鈴薯畫了個遍,這種好心態,讓他的人生也變得有趣而豐盈。
周國平說:獨處是靈魂生長的必要空間,在獨處時,我們從別人和事務中抽身出來,回到了自己。
孤獨期,其實也是人生的蟄伏期,讓自己的內心變得強大起來,懂得從生活中尋回一點力量,才能從容面對自己的將來。

在孤獨中蓄力,以自己喜歡的方式過一生
看到過這樣一句話:無論是想爭取成功,還是改變命運,大多數人都會經歷一段靜默的時光,在孤獨中積累和蓄力,安靜地找到自己人生的方向。
是啊,每個人的生命長度不同,我們沒必要去模仿別人,羨慕別人,就像《遺忘清單》中的愛德華.科爾和卡特.錢伯斯一樣,為自己活一次,去做這輩子覺得遺憾的事。
在電影中,他們結伴去跳傘,在長城上騎摩托車,去看埃及的金字塔,去埃塞俄比亞看野生動物,然后把最后的時光留給了家人。
曾看到過一項對老年人的調查研究。
研究人員問老人們:你們一生中最遺憾和后悔的是什么?如果生命能夠重來,會做什么不同的選擇?絕大多數人回答:會去做想做而沒敢做的事。
人生后悔想做沒做的事,遠遠大于做錯了的事。
我們都可以按自己喜歡的方式過一生,在孤獨中陪伴自己,充實自己。
因為我們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個會先來,與其過一種平淡重復的人生,不如給自己列一份愿望清單,逐一去實現它,去尋找平凡生活中的小確幸,去感知人和人之間的有趣相遇,去旅行,看這個奇妙的大千世界,去做自己不敢做的事情。
趁早行動起來,才能讓自己貧乏的生活多一點色彩,以這樣的姿態,就無懼于人生的終點。
劉同曾說:孤獨是一個沒有明確答案的名詞,是多種情緒的化身,是一個人必須要面對的很多事。正在經歷的孤獨,我們稱之為迷茫。經過的那些孤獨,我們稱之為成長。
是啊,生活中的我們常常為社交所累,刷不完的手機,走馬觀花似的飯局,似乎無時無刻不在把我們的生活割裂,我們被生活追趕著,害怕下一秒就和這個世界脫軌。
其實人生更應該擁有的,是一種簡單的幸福。讓我們的物質生活和人際關系處于最簡單的狀態,才能讓心靈擁有更廣闊的空間。
因為孤獨,也是我們認識自己的最好機會。